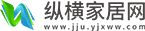环球百事通!【散文随笔】去乡下过年
老家,在这片土地的千千万万打工人眼里,一旦提起,一般都会冠以之眷恋,依恋,思念等等名词。但对我而言则不是。出生在超一线城市的我,因为家庭缘故,从未去过父系那个很近的故乡;自小放寒暑假,我都去的,是母系那里的故乡,那座曾停靠着受那位白衣美男子指挥的浩荡舰队的吴文化的都城。时过境迁,那些辉煌当然都早已往日不再了。
那个时候,外公外婆总是带着我到处去玩,幼年的我觉得这座城虽然没有省会城市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诗意美景,但这座城同样曾隐居着一位名士,而住所阳台盛开的兰花,意味着这座城一样有我所追求的东西。但这段记忆在外公大病后便中断了,过世后更是消逝的无影无踪。是的,眷恋的人去了,依恋的景消了,思念的城自然而然地塌了。对我而言,这个地方不过是寒暑假的庇护所,庇护者去了,埋藏在这座小城底下的,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便揭露开。我想,没有人喜欢在经过一个学年的繁重学习或是全年无休的生活拷打之下再来一个陌生的地方被不和你天天在一起生活的人指手画脚吧?所以便不再回来。之后,浩劫席卷了这片大地,是意外还是意内小民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不再需要寻找借口到这里。直到一个清晨,我早上起来,我妈跟我说,她奶奶托梦让她回去。我不知道真的假的,神鬼托梦之说不应该存在于这片赤红的土地之上,但,对不可知之事还是敬畏为好,再算上确实很多年没回去了。所以,即使在这里还有没结束的事情,我们还是决定回去。对于出发点就在家门口的车站而言,八点半开车七点出门未免太早,意料之内的早到了去买杯咖啡却发现红色的咖啡厅已经关门,只能转投对面,开设时间更长的绿色的咖啡店。冷冷清清的咖啡店映衬着热情的店员,但咖啡的品质无愧于刷锅水之名。慢慢悠悠从熟悉的地道走到陌生的车站,排队进站倒是刚刚好赶上验票。
爬上车,复兴号电动力车组,或者我和我妈开玩笑的“复兴号级”动车的一等座比想的要窄一些,座位总体还是舒服的,但要带着口罩去隔绝不可知之物,还是闷热无比。雪上加霜的是我把原来打算重温的电视剧下错盘了,不在带出来的移动硬盘或是这台电脑里,丰富多彩的七小时车程变成了牢狱之灾,好在还有带出来的书聊以解乏,再不行还可以睡觉。雪上加霜神兽上车了。我无比后悔带的书是高深的外文,而嘈杂闷热的环境几近我描写下的交融环境。大概是早起的缘故,还是累的不慎睡着了一会,醒来,口罩里全是口水。终于熬下了车,说好来接的人在外面应酬,而打车来的替补也来不了,只能自己打车回去。司机师傅十年如一日的热情,带着我们回到了那个同样由著名将领命名的小巷子里。时过境迁,曾经的华润万家已被当地的超市巨头替代,被拆陈一片瓦砾的土地上大楼拔地而起,包围着小小的岳师门,而北司诸支巷的石板路也被替换上了城市味更足的沥青。但有些尘土的路段,我觉得、这里没有特色,反而很像我所住的城市的郊区。
 (资料图)
(资料图)
我提着行李箱,缓缓地走进熟悉而陌生的巷子里,现代的高楼公寓环绕着老式的大院垣墙,让我有点疑惑,这是不是以前我印象里的庇护所。是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更何况是八年之别。无论我是否使用哲学,这里都不再是以前、我记忆滤镜下的那所庇护所。
老式的防盗铁门,锈迹斑斑,护着里面,新式的防盗门,我按下门铃,叫声“外婆”。向左转去,高不可触的玻璃橱窗里多了一张和记忆中截然不同的照片,而老外婆热好了他们叫“粑”的一种米制的团子,给我们充饥。随后是惯例的嘘寒问暖。
等舅舅一家子回来上桌吃饭,饭后,他问我要不要去他合作伙伴开的三温暖洗澡,我和母亲都拒绝了,他问我:“你不要社交了?”,我摇摇头,奔波的疲累战胜了本就不强烈的社交欲望,而且 。等他们出去了,我那稀里糊涂的老外婆才告诉我,浴霸坏了;同是厕所的浴室又不能关上窗不通风,无奈之下只能擦擦弄弄,将就着上床睡觉。
大年三十,惯例要下乡祭祖,早睡自然早起,生意人回乡的舅舅晚睡也撑住,沿着高速路向下,路边的风景也从城变成了乡。在动车上那段无聊的时间里,我们看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乡下的房子,都是和城里连排的截然相反的小独栋。无数茶余饭后的谈资都告诉我,这些地方的人们辛辛苦苦去大城市赚钱,回乡起屋,希望能改善生活,但他们所挣的可能还不到在办公室里舒舒服服的文员的一个零头。
黄家村和这些谈资里的故事一样,大年三十的清晨见到的不是老就是少,中青寥寥无几。大抵是响应号召不回,又或是省一点钱?我无从得知。跟着他们走走,尝试修补因为一些事破损的关系,但亲戚们很热情,东家拉我去菜园割点菜,西家拉着我去吃点“粑”,南家拉着我去拿点土鸡蛋,北家塞给我一个红包。他们仿佛在告诉我,大人的事是大人的,和小辈无关。
磨磨蹭蹭终于踏上祭祖的路,石板路随着路过菜园和新建的铁轨而变得荒芜,小河畔,妇女如同母亲小时候那样用石头摔洗着衣服,他们没走大道,我们家的坟地不像我写的那样在大路的尽头。二舅公拿起砍刀,以七旬不该有的勇武,劈林开路。
我方知古人要多生儿子,除了学到的增加劳动力、分配田产、多投资以获得回报、抵抗风险等等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继承香火。我跟在队尾,慢慢的走,心想完全在城里长大的,不要说孩子,哪怕是成年人,也难以承担这种级别的粗活。
小路逐渐地被打开,而山坟就在前面。大人们都上去清理其他的坟地了,留我照看外公的。
我清扫着外公坟前堆积的破败尘土,嘴里开始不自觉的喃喃自语。
“外公,七年还是八年了,回来了。我们这脉隔了一代的第一个全日制大学生,虽然本科不是很光彩,但至少辅修给我运气中到了,历史系啊,历史系啊。”
我叹了口气,蹲下来,帮舅舅和母亲点起他们买的软壳中华。
“我不知道当年你让舅舅考理考成那样有没有后悔过,我知道你对这个儿子很满意,是的,他至少自力更生了,他也在你最后的日子帮到你不少,但我知道你对病痛的现实妥协的背后,始终是希望我们家有一个读书人。”
软壳中华很细,不至于呛到我,我点完一排,去拿另一排。
“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路会在何方,甚至很难向你承诺什么,也许我唯一可以保证的是,我这一房传承,一定世世代代都是读书人。”
我还想说,但大人们劈完了上面的枯枝,慢慢走下来,要放炮仗,祭祖,我便退到一边,静静地看着。等到去吃年中饭,再到去吃年夜饭,慢慢的再到守岁,亲戚们很热闹,而我没有再说什么,问道什么,回答什么。
我在观察,我想从这些形形色色的亲戚那里,读到我如何履行我对亡者的诺言的答案。他们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事,,但到了这个特殊的日子,他们还是会回到这个小巷子的餐桌上,进行似乎是刻在基因里的事情。我从他们每个人的谈吐间,每个离席去打的电话里,每个提起的看似牛逼哄哄的社交,每个所谓的小道消息,都读不到过年的开心。相反的,我读到了一种为生活奔波的疲态。
我不记得在哪里听到过一句:“当你觉得过年很累的时候,你就长大了。”
是的,看到他们这么累,我也觉得很累。而且,我也没能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回到大城市的家,我深呼吸了一口气,对着母亲。
“我们明年还是不回去了吧。”